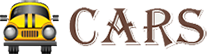“科学”一词,唐代就有,原指科举之学。唐朝诗人罗衮撰《仓部柏郎中墓志铭》就有“近代科学之家”一说,其意为:唐以来致力于科举之学的家庭。
奈良时代,日本唐化,把科举制也拿来了,用了好几个时代。到了江户时代,就行不通了,改以“学问吟咏”。当然,也有人说,它是“江户版的科举制”。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科举制被取缔了,江户人放下了一个历史的包袱,却留下了一种制度的优雅。
总之,近代以前,日本已无科举制,亦无与之相关的“科学”,但这并不妨碍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拿它来对译西学。
当“科学”在日本兴起时,“科举之学”还在中国保留,直至20世纪初,清朝将亡而告终。期间,“科学”一词,经由明治人维新以后,回流中国,以“分科之学”取代“格致”。
中国传统里,早有“格物致知”一说,其说最早出自《礼记·大学》“八目”中的“格物、致知”二目。宋儒以“格致”入《四书》,而为“格物穷理”说,并开启“格致之学”。据董光璧《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所言,北宋“格致”第一书,为《格物麤谈》,是一部博物学著作,其后,有人为朱世杰《四元玉鉴》作序,亦将其视为“格致之学”。
元时延展,元人朱震亨将其医著名为《格致余论》。明时尤盛,不但李时珍将本草学称作“格物之学”,其他如明曹昭以文物鉴定作《格古要论》,胡文焕辑古今考证成《格致丛书》等,当西学进入中国,便以“格致之学”来对译“science”了。
科学一词,其本义,出自拉丁语scire,其名词形式为scientia,进入法语后,以法兰西人发音,演变为science,意指“自然知识”,后入英语,science演变为科学。
由于古汉语中缺少与“science”对应的词语,故明清两代学人便以“格致”对译,最早这么译的,就是徐光启。1607年,他在《刻几何原本序》中称赞利玛窦,“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也就是“科学”。
受其影响,传教士亦如法炮制,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作《空际格致》,以“空际”名自然,为“自然格致”。以其言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说,可见其为“自然哲学”。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译《坤舆格致》是关于矿冶学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康熙帝《穷理学》60卷,乃当时来华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总汇。
王扬宗在《汉语“科学”一词的由来》中这样说道:用“格致之学”对译西方科学有一大好处。好处何在?原来,中国人对西洋事物不逊,早期译名,都要加一“口”字偏旁以示轻蔑,多亏徐光启,用了“格致之学”这样一个好名字,为西方的科学“正名”,这才在中国立住了脚跟。
那时的日本人跟着中国亦步亦趋,也开始接触西学,因为当时的荷兰人号称“海上马车夫”,纵横四海,万里远航,来到东洋,虽然受挫于中国民间海权,却吸引了日本的目光。于是,汉学以外,兰学新开。接着,英国打败了荷兰,英文接踵而来,科学取代兰学,日本开始了科学的历程。
当“科学主义”已在日本泛滥时,中国士人却依旧陶醉在明末清初的思潮里,从徐光启主张的“中西会通”转入到“西学中源”去。
“西学中源”说,与“格致之学”相辅而行,然其初亦不为无据。明中期以后,洋帆东渡,西学亦来,滔滔而至者,或持币,或操船炮,或奉天主,都是手握利器,逐利而来。
当其还时,又岂能空手而归?无论丝瓷茶,抑或儒释道,都被来者带回西方,尤其中国王权及其国家样式,仿佛天然文艺复兴款,深受方从政教分离中解放出来的欧洲国王的欢迎。如何做君主?光有一本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不够的,还要参考两千年来经久不衰的君主制的中国样板。
于是乎,“中国风”在欧洲宫廷里流行起来,不但消费主义的东方文化品位登堂入室被请入贵族之家,连国家主义的代表孔夫子,也成了来自中国却被欧洲关注并接纳的哲学家。而推崇中国文化的西哲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则被人称作“欧洲孔夫子”。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希腊乎,中国乎”欧洲向何处去?
于此背景下,而有“西学中源”说。此说起于明末,清初得以传播,连康熙帝都来发圣旨,说“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西洋算法原系中国算法”,这样说来,除了文化的偏执,还有国家的傲慢,皇帝说了,谁敢不信?
于是拿出“证据”来,有人从《史记》里找了一句“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还有人提到孔子说过“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样,西学就成了中学的“后裔”。
其时,较有分量的两部书,值得我们一提。一部是康熙时期陈元龙的《格致镜原》,百卷,30大类,子目千七百余,举其内容,上及天文,下涉地理,无物不包,无器不具,能以“格物”之博学,发“致知”之深思;另一部,是乾隆时期阮元的《畴人传》,46卷269篇,记述上古至清嘉庆年间天文、数学、历法等方面的专门学者275人,另有西洋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41人。
在书前凡例中曰:世袭之业为“畴”,师承家学为“畴人”,故“是编以‘畴人传’为名”。阮元本人也是一位“畴人”,对“中西异同,今古沿改,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颇有兴趣,认为“数”为六艺之一,“儒者之学,斯为大矣”。其《畴人传》序曰:术数之妙,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
阮元将西方科学纳入考据学,他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儒流实事求是之学”,另一个是“融会中西之学”。因此,科学能以“格致”之名,普及于中国。
然其弊在于,偏离了科学方向,没有走向实验与数学相结合,而是从中国的古代文献里寻找西方科学源头,把科学变成了考据学,在经史子集的中国传统里,被乾嘉考据学淹没,其后,虽在洋务运动中复活,但已转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
从徐光启到阮元,尚可见“格致之学”的初心,亦即中学与西学本来“会通”,在“会通”中,可以“融会中西,归于一是”——成其一种如莱布尼茨曾经追求过的“世界科学”。
徐光启言及利玛窦时,言其一人兼具三学:“奉天事主”,神学也;“格物穷理”,当为理论科学;而“象数之学”,则为应用科学或技术,二者统称即“科学技术”。原以为,徐氏划分,基于中学传统,后来发现,它出自《西学凡》,“西学”之名于中国正式发表,始于是书。
是书分为六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作者艾儒略,亦传教士,利玛窦死后来华,沪上传教时曾寓徐宅,得徐氏相助,故徐氏之于《西学凡》可谓深知,其“格物穷理”说,就出自《西学凡》的“分科之学”第二科“理科”。
是书虽未以“科学”为名,却带来了一个科学体系,由此可知,中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了解,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了,原不必待两百年以后让日本明治人来抢“科学”风头。
于是,难免一问:何以万历人以及那时的传教士们,不以“科学”为名,而以“西学”相称?对此一问,我们认为:一来,中国早有“科学”——“科举之学”,故当避之;二来,西学东渐和欧洲启蒙时代“中国风”,共同培育了那时的一个理想,一个以“孔耶同源,中西会通”为代表的世界统一性的理想。
那是17世纪全人类的一个最伟大的理想,不但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在欧洲宣示了这一理想,就连洛克也将他的《中国笔记》放在了他在英伦的案头上,作为他写作《政府论》的参考。而一波又一波的传教士们,则将这理想带到中国来了,他们穿戴中国士人衣冠,好一副中国书生模样,而经历了心学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国启蒙时代的士人,也为他们到来,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除了徐光启,还有李之藻等晚明士人,他们投入天主怀抱,接受宗教洗礼,与其说是因为信仰,而毋宁说是为了东西方启蒙时育的那个世界统一性的理想,竟然全身心投入。他们同传教士一起,在中国思想的领空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孔耶同源”,那是神学大旗,一面是“中西会通”,那是哲学大旗。两面大旗,就一个风向,那就是“会通”。
“孔耶同源”,是中国天道与西方天主的“会通”,而“中西会通”,则是中学与西学的“会通”。正是在这两个“会通”中,孔子成为了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个世界性的哲学家,而且中学与西学的“会通”,在哲学上达成了“格物穷理”的共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对《西学凡》的“六科提要”,“凡也者,举其概也”,也就是“提要”的意思,“提要”如下:
以“小学”言“文科”,把“文科”说小了。清初“小学”,指的是考据学工具箱里必备的学术工具,诸如基于音韵学和训诂学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而“文科”范围,当不止于此。“理科”也一样,用“大学”说“理科”,就把“理科”说到《大学》“八目”里的“格物、致知”两目上去了,这样一来,“理科”——理论科学,就被说成了“格致之学”。
其余如“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这是指文、理二科的应用科学。而“道科”为神学,言其“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至命之极也”,这就说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里去了,总之: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
由此可见,官家《四库全书》已经认可了“西学”,并在“格物穷理”这一点上,同《西学凡》达成共识,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以“格致之学”为标志的东西方学术共同体建设。
明人杨廷筠在《刻西学凡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有关西书七千余部的说法,因为他听说了有“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而《西学凡》,有可能就是对这七千余部西书的提要。艾儒略本人,在《西学凡》中,也言及西书入华“旅人九万里远来,愿将以前诸论与同志翻以华言,试假十数年之功,当可次第译出”,而《西学凡》也只是他为此目标开了个头。
“西学”之名,虽由《西学凡》问世,但率先提出来的,并非艾儒略,而是高一志,他先于艾子作“西学”一文,以此介绍西方教育体系及其知识构造,却因“南京教案”而入狱,被遣返澳门,故未刊发,后收该文入其《童幼教育》一书中。
晚明士人中,最早接受“西学”一词并撰文表示的,是闽人叶向高。艾子早有入闽打算,因闽地“山道崎岖,语言难晓”而未果。适逢叶氏退职归里,途经杭州,二人于杨廷筠寓相识,便随叶氏入闽。其时,刚好《西学凡》在杭初印,叶氏因之而能得此“西学”风气之先,故亦作《西学十诫初解序》一文。
这是中文里,最早出现“西学”一词的文章。应知“西学”初来中国,并非来与“中学”对立,而是来与之相应,这是中西文明相互包容、惺惺相惜的表现。
万历时期,不但西方流行“中国风”,而且中国掀起传教热,那时,明朝的高官可以入教,可受洗礼,传教士也可以来到皇帝身边,在皇帝身边传教,并向皇帝讲解“西学”。从万历到康熙,中西文化交流有过这么一个蜜月期,可惜的是,这个蜜月期因教会内部分歧,被教皇终止。
终止的原因,是由于礼仪之争,教会对中国人“祭天、祭祖、祭孔”看法不一,带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传教士认为,“中国三祭”属于自然神学,而偏向宗教信仰的传教士则认为是无神论,最后,由教皇来裁决,教皇决定脑袋,定为无神论。
就这样,导致了趋于统一性的东西方文明的一次大决裂,在西方,中国风变成了反中国风;在中国,传教热变成了反洋教运动。中学与西学,从同构转向脱钩,从对应转向对立。
《西学凡》便是中西同构的产物。从中,我们可见艾子基于对自然神学——天理、天道的认同,而对中学与西学所作的同构——理科、道科设置。如果说“理科”是自然哲学,那么“道科”就是自然神学,在当时的西方学术规范里,科学从属于哲学,哲学从属于神学,而自然神学就要从天理、天道走向天主。
可惜了!中西不通,格致道断,艾子“西学”搁浅,止于“提要”阶段,原来预计花十几年时间翻译7000余部书的计划,就此打住,清初学者,转以西学入考据而为“西学中源”。
然而,在日本,却未有此等“西学”烦恼,西方传教士不会跑到日本去称“西学”,因其文明的分量和体量都不够,在东西方文明的天平上,能代表东方来与“西学”作对称的,唯有中国和“中学”,这是西方的特许——被西方认同,也是中国的特权——可以挂“西学”牌,开“中学”店,以此“融会中西”。
而日本之于西方,则不具有文明整体的代表性,故其着眼于具体,分地域,择取国别以称之,而有其“兰学”、“英学”;分“学域”,择其学科以名之,而有其“分科之学”。从“分科之学”出发,使“科学”脱离学科的局限,取代“格致之学”,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则是日本人的功劳。
就这样,“科学”的概念出现于明治时期,始于1874年的明治七年左右,最早使用这个词的,还是福泽谕吉。其本义,指“分科之学”。科学之“科”,意味着学术专业或学问领域,以及确认各科学问的专业范围,因此,“科”是一种研究性的分类方法;又,在分科的基础上,每一学科必须以实验为前提,作为究明事实的实证性方法论,方可谓“科学”。
福泽谕吉《劝学篇》说,明治时期“科学”已不容置疑,伊始,人们对于科学,怀有宗教般信仰的感情,任何事物若不加以“科学性”的说明,人们就不会相信,若被判定为“非科学性”,那就等于宣判其非法,并且剥夺其存在的合理性。
“科学”虽非由日本人创造,而是从中国文化捡漏,但他们确实捡到了宝,“科学”之于清朝,不但明珠暗投,投到考据学的深渊里去了,而且走错了道,往“西学中源”上走了。
以福翁之博学,他当然知道中国传统学问里的“格物致知”,并且应该懂得明清以来的“格致之学”,他为什么不走中国老路驾轻就熟?也许他看穿了这条路——此路通往“西学中源”,“中源”一出,科学就走到了尽头,这叫做“走科学的路,让科学无路可走”。当然,此在清朝,“科学”被溯源至《考工记》了。
在一本失传的《考工记》里,科学还有路可走吗?在科学史里,“科学”失踪,过去找不着,未来没有了。于是,福翁告别“格致”走自己的路,走向“一科一学”。他不但分科,还为各科下定义:所谓地理学,是日本国乃至于世界万国的风土向导;所谓物理学,是一门考察天地万物的性质并探知其动向的学问;所谓历史学,就像一部书,以年代记载、详尽诠释、索引万国古今的情状;所谓经济学,与其说事关一身一家一户,而毋宁说是总天下为一户的生计;所谓修身学,主要强调尊重人的本性,以阐明与他人交往处世的修身之要。
正是“一科一学”,成就了日语“科学”一词。本来,科学就是科学的事,分科而已,无需国家主义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