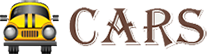8月12日,苏州金鸡湖美术馆,“天际线——管怀宾作品展”还在紧锣密鼓地布置,第二天就是开幕日。仍记得启门初访时,展览前言刚为“乌托邦的想象”几个字印上句号。展厅内,两件巨物一横一纵,安如磐石。然而,站在那些庞大的作品前,我短暂地失去了言语的诉求,倒不是因为这些作品晦涩难懂到无言以对,而是相比我能说的,或许它们想说得更多。
“语言是否具有火药的穿透力、杀伤力,在于它是否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和配比……”8年前,在与诗人泉子的访谈中,管怀宾这样回答了关于艺术媒介的问题。
实际上,当被问起自己的艺术所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时,管怀宾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诗歌。应该是诗歌、诗歌的修辞、情感、叙事,还有它时间、空间。这些都和装置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诗歌对于管怀宾的创作意义重大,他曾不止一次在访谈中自述。“我在很多场合一再强调装置与诗歌的内在关联,诗歌应该是给我启示最大的一个艺术门类。虽然装置艺术是有关物与物、物与空间、物与时间、物在特定场域中的种种关联与矛盾状态形成的空间情境,并由此诉诸观念与思考。但无论是现成品还是自造物,包括空间与场所本身,它不再是客体化的物理存在,它们的自然属性在装置创作中常常是被异化、消减或者强化到一个崭新的语境轨道,就像诗歌中的文字被赋予新的指涉和语意。”
在大多数人看来,老管的确像个诗人,一个跨媒体诗人,一个用重金属、声、光,电等材料写就诗篇的诗人。对他而言,选择装置的器物与经营作品的结构或许与诗人的遣词造句遵循相仿的规律。正如他的老师坂口宽敏对他的评价一样,管怀宾这些年一直在艺术上探索凝练着艺术的语言,他赓续着自己的“园语”,写下了一首首送给彼岸的诗。
在本次展览第二展厅的《光阴·天成》系列作品中,展台上体量不大、姿态各异的装置便是艺术家平日里“日常写作”的见证。根据管怀宾介绍,这些作品呼应了上个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的创作,它们像是续写给当年先锋派对未来理想的诗歌,自己的作品还更多地思考了不同于西方人的空间构想,关注于东方艺术中“势”与“象”的建构。
对于“筑梦”,老管向来是一个行动的理想主义者。为跨越日常经验,捕捉到这些灵感,乌有之乡的“钥匙”被老管造了百把,细细数来一共一百零六件,它们是艺术家过去一年半里的劳作记录,此刻正高低错落地静置厅内。
“我觉得在这些作品里面,它们把我的那种庞大的‘无人界’,或者说那种共通性的装置的构想,又带到了一种相对比较私人的写作上面。”
估计谁也想不到,这一说来文雅的“私人写作”背后,其实是一种类似工人般的劳作。在管怀宾工作室内的一间小房间里,各式各样的金工器械被整齐摆放墙上,台虎钳上还夹着尚未完工的装置;而桌子的另一边,则是艺术家平日里收集的眼花缭乱的金属原材料——加热管,散热器,单簧管……某些甚至很难叫上名字。而这些不过是他居家办公时的阵仗。
记得那天去拜访管怀宾的“艺术工厂”时,他正在弥散着金属粉尘的厂房里协调工人搬运展品。看到我们来了,他便一个劲地“赶”我们:“你们不要在车间里面待太久,空气里都是铁屑……”可随即,他自己却消失在八月蒸笼般的车间里,忙碌到根本顾不上采访。直到后来装车完工,他发现自己汗涔涔的囧样,便向我们幽默地揶揄了一下自己“估计你们还没有见过哪个艺术家像我这样工作的。”
当我们再次回到这些“日记”:弯曲的铁喇叭,铜绿的太湖石,折叠的电熨斗……人们可以想见它们背后那高于生活,又低于玄想的创作历程,它们都是管怀宾日日描绘的“天际线”,象征彼岸,却也近在眼前。
对于这次展览中的一些作品导览,管怀宾本人把握着一定阐释的限度。他站在那件体量庞大的展品《雷惊海》前说:“在这件作品中,无论是弯曲的聚能管、还是褶皱的铜喇叭,抑或是锈蚀的太湖石,它们其实并不屈从于一个固定的含义,就像这个弯曲的铜管可以像是一个闪电,也可以像是某种汇聚能量的加热棒,它们往往并不是一个直白的代表,只能说它们之间的某种线索在整体上共同构成了一种语境和创造。”
在展厅射灯的照射下,这件装置的投影恰好在墙面上映下一座黑塔般的剪影,与眼前的喇叭相差甚远,类似的细节还有经过镜面反射的如水波般的光线,以及映照墙面如园林月洞门的强光,它们以诗意钝化了所有人心中渴求的固定阐释,也让思考重新睁开眼睛。我想相比教人怎么去看,管怀宾更希望让作品自己言说。皓信生物驻马店美术家预制建筑:装配式建筑行业平台直流稳压电源乌有之乡三众弹性技术是一家专业研发